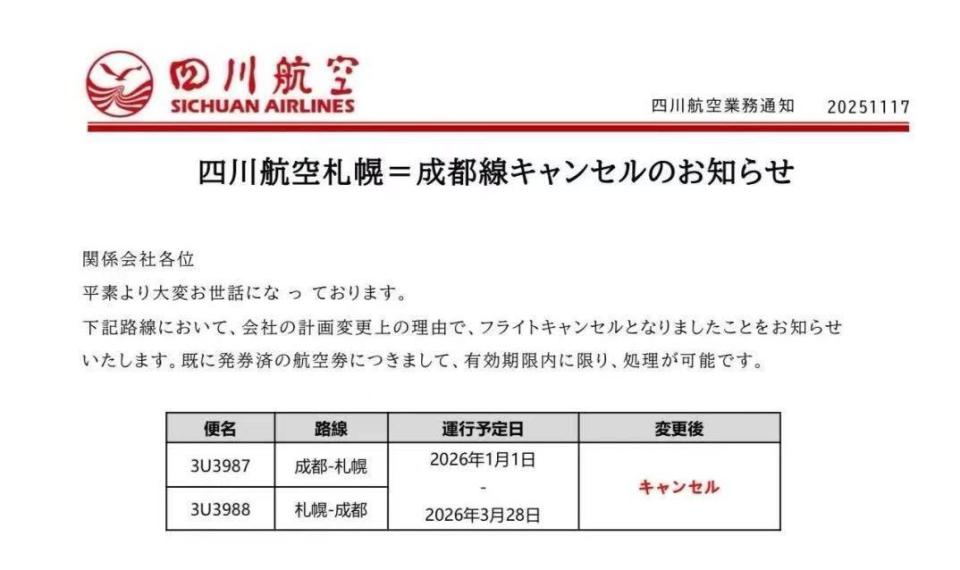11月14日的长沙街头,风裹着细碎的雨丝。湖南省直中医医院门诊楼前的梧桐叶落了一地,护士魏珊攥着言纲主任上周递来的“患者陪护清单”,指尖把纸角揉出了褶皱——那个总说“病人的事比啥都急”的人,怎么突然就不在了?
48岁的言纲是这家三甲医院胃肠烧伤外科的“顶梁柱”。2001年从天津医科大学毕业后,他考了中山大学的硕士,2011年主动援疆去了喀什,在戈壁滩上的医院里守了一年,帮当地牧民做了30多台疑难手术,回来时晒得像块黑炭,却笑着举着“优秀援疆干部”的证书说:“值了,至少让那边的医生学会了肠吻合术。”2025年3月,他又扎进了永州市东安县第二人民医院——这个距离长沙200多公里的县级医院,成了他最后奋斗的战场。
同事们的记忆里,言纲的“忙”是刻在骨子里的。11月12日上午9点,他穿着手术服站在东安县医院的手术台边,手里的手术刀稳得像定海神针。那是台胃肠肿瘤切除手术,要避开腹腔里的大血管,他一边操作一边给年轻医生讲:“这里的脂肪层要慢慢剥,不然碰破了肠系膜上动脉,止血要花半小时。”3个半小时后,手术结束,他摘下口罩时,下巴上的胡茬都浸着汗。中午和同事吃食堂的辣椒炒肉,他还开玩笑:“今天的肉比昨天嫩,晚上要是不疼了,咱去爬东安的舜皇山?”
可疼痛没给这个“铁人”留余地。当天上午,言纲就跟支援同事提过“胸腹部有点闷疼,可能是老胃病犯了”;晚上8点,他疼得直不起腰,打电话喊同事送医——急诊CT显示,急性前壁心肌梗塞,血管堵了90%。13日深夜,这个总是把“再等等,把病人的药换完”挂在嘴边的医生,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“前一天还一起吃饭的人,怎么说没就没了?”告别仪式上,年轻医生小陈抱着言纲的工作证哭红了眼。护士长魏珊想起上周的事:一个外地来的阿姨没钱买陪护床,言纲掏出200块塞给她,说“我是医生,这点忙应该帮”;援疆时的老同事发来消息:“当年在喀什,他为了给哈萨克族老人做胆囊手术,连续3天查资料,熬得眼睛通红,却说‘病人等不起’。”
11月16日,湖南省直中医医院的走廊里还飘着言纲喜欢的茉莉花茶味——他的办公桌抽屉里,还放着没来得及寄给援疆孩子的笔记本,扉页写着“好好读书,以后当医生”。同事们说,言主任的“傻”是出了名的:支援东安时没拿过补贴,说“我是来干活的,不是来拿钱的”;门诊时遇到没钱的病人,总把自己的诊疗费免了,说“治病要紧”。
风里的雨丝越下越密,言纲的照片挂在医院的“优秀医生”墙里,嘴角还带着笑。那个总穿着白大褂跑前跑后的身影,终于“歇”了,可他留在手术台、病房、支援路上的热乎劲儿,却像一把火,烧在每一个被他温暖过的人心里——就像他常说的:“当医生的,一辈子能多帮一个病人,就没白活。”
而这一次,他把最后一份“帮”,留在了自己最爱的岗位上。